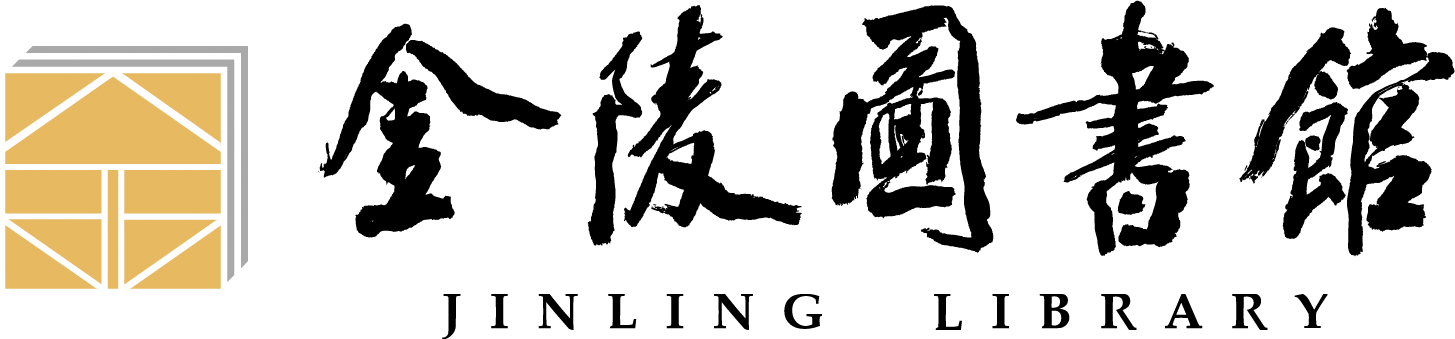◇刘周岩![期刊架位号[8153] 期刊架位号[8153]](./W020240310542942912537.png)
“迅行”是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时使用的笔名,以激励自己在进步的道路上迅疾而行,他有意在《狂人日记》这篇沉寂近十年后的呐喊之作里借笔名重拾年轻时的信心与希望,但《新青年》编辑部又不愿让他署这样一个别号一般的名字,于是他添上了自己一向敬重的母亲鲁瑞的姓。“鲁迅”这一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史中最重要的名字就此诞生。
自此之后,周树人以“鲁迅”的笔名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译文等,一共超过五百篇,这成为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笔名。但鲁迅并不仅仅是“鲁迅”,他还是“雪之”“封余”,是“白在宣”“隋洛文”,是“宴之敖者”“楮冠病叟”,乃至是“ELEF”“……”等,鲁迅所有的笔名一共超过一百五十个,在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罕见。正如鲁迅本人所说,“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鲁迅一生中众多的笔名正和他的思想动态、人生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鲁迅一生中的第一个笔名是“戛剑生”,用于1898年十八岁时写的一些文言诗文。戛,击也。“戛剑生”即击剑的人,表现的是一种渴求战斗的激情。鲁迅青年时期用的数个笔名都是表示这种奋发的心态与自我激励。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翻译了科幻小说《地底旅行》,用了“索士”的笔名,即探索之士。鲁迅当时颇信奉梁启超的小说可以教化国民的理论,又尤其看重科学,于是成了中国最早一批翻译科幻小说的人,以此来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日本期间鲁迅还使用“令飞”“迅行”的笔名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早期论文,均取奋飞、疾驰之意。
回国之后不久,辛亥革命就爆发了,鲁迅一开始期望颇高,在民国元年以“黄棘”的笔名为《越铎日报》写发刊词,取“以棘策马,驱之迅行”之意,号召大家“同力合作,为华土谋”。可是很快,现实政治的发展就击碎了这好梦,辛亥革命后黑暗还是照旧,而且多了许多新的荒唐。这失望与颓唐就一直伴随着鲁迅。从1909年鲁迅由日本回国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间的近十年,除了那一个“黄棘”,鲁迅再未起过任何笔名,仅有的几篇文章都以“周豫才”这一最初的学名或“树”“周树”等名字的简写发表。
直到钱玄同来找鲁迅给《新青年》供稿,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前夕发表的《狂人日记》成为转折点,自此之后,鲁迅便一发不可收,几个月之内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药》《我之节烈观》等一系列著名的小说和文章,并由此终其一生保持着高产出的创作。
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作品大多是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的,不过每年都会有两三个新造的笔名,这些临时的笔名往往是为着某种专门的讽刺目的而单独使用在一篇特定的文章中。
“雪之”这个笔名专门为了讽刺章士钊,仅见于杂文《“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士钊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二桃杀三士”的例子,嘲讽白话文只能表达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以此提倡文言文。可“三士”的正确解释应为“三个勇士”,章士钊弄错典故闹了笑话,鲁迅便以“雪之”为名,表示要还“二桃杀三士”这句话的清白,以此讽刺提倡旧文化却自身根基不深的章士钊。
鲁迅也常因别人对他的称呼而起一个相应的笔名。高长虹曾攻击鲁迅“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鲁迅便在回击的文章中署名“楮冠病叟”,楮,即纸,“楮冠”对应“纸糊的假冠”,“病叟”对应“身心交病”。有人曾骂鲁迅是“封建余孽”,鲁迅便依样用“封余”的笔名,作文回击。除了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情形,鲁迅也在和亲近的人的通信中偶尔用些特别的名字,或幽默或亲密。因爱人许广平亲昵地称自己为“小白象”,鲁迅便用“ELEF”署名回信,这是德文大象“Elefant”一词的简写。朋友钱玄同主张废姓,鲁迅是不同意的,他于是便以省略号“……”作为回信的署名,幽默地表示自己的反对,因为按钱玄同的意见,那么表示“姓鲁名迅”的“鲁迅”便是不宜使用的。
在整个二十年代出现的笔名中,最为特别也最为重要的一个是“宴之敖者”。1923年7月14日下午,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绝交了,普遍认为和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有关。兄弟二人失和后的第二年,鲁迅首次使用了“宴之敖者”的笔名。据许广平说,鲁迅本人对这一名字的解释是:“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
三十年代,鲁迅的创作已经转向,他把大量的精力用于论争性的杂文写作上,这也直接导致他使用了一大批新的笔名。鲁迅一生中的大部分笔名都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从1930年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使用的笔名超过一百个,其中仅1934年一年就使用了多达41个新笔名。直接与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隐藏身份、逃避审查。鲁迅的文章是高度政治性和批判性的,这是为当局所不容的,白色恐怖时期因言入狱乃至被暗杀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鲁迅本人也在被通缉之列,但鲁迅是坚持战斗绝不退缩的,他于是便“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
鲁迅当然也不会忘了借着起笔名的机会嘲讽当局和论敌。“白在宣”是指对手“白白在宣传”,“敬一尊”则是“回敬一杯”之意。颇为幽默的两个是“隋洛文”与“何家干”。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于是鲁迅便变换字形,由“堕落文人”取了个“隋洛文”的名字,并且发文致浙江省党部,为其“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表示感激“党恩高厚”。鲁迅在集中抨击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20多篇最为敏感的政治时评中,故意署名“何家干”,即“谁做的”,毫不留情地挑衅封杀言论的政府当局。鲁迅本人说取这些笔名是为了使将来的战斗的青年看到时,能够“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1936年8月,鲁迅的病情急剧恶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临终前写了数篇《立此存照》,均以“晓角”署名,即黎明前的战斗号角。许广平对鲁迅这最后一个笔名如此评论:“先生最后用的笔名,载在《中流》上的是‘晓角’二字,他最后还不忘唤醒国人,希望我们大家永远记取这一位文坛战士的热望。”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抉择,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主题,鲁迅在临终的最后时刻,选择给后人以“晓角”的希望。
从“戛剑生”到“晓角”的这一百五十多个笔名,也正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领导文萃》2024年4期 期刊架位号 [8153])